赠霍渭先进士毕姻归南海长律一百韵
发迹青云上,收身紫极边。相逢何恨晚,倾倒到忘年。
溟海千龄鹤,风波万斛船。是源终必达,若火势方然。
斗极应长定,星霜却屡迁。哲人无习气,圣学谢陈篇。
四宇云消尽,中天月自圆。有流皆赴海,无地不同天。
锻炼功须此,山林趣已偏。百途皆适国,一苇亦杭川。
尺蠖时乎屈,羚羊有或悬。陆沈须似朔,勇退每思钱。
敝帚真谁售,兰膏合自怜。侧身观世界,引手汲天泉。
铁笛吹何处,蒲团坐欲穿。前程无税驾,重任未弛肩。
在水应为润,存规必作员。一心从主宰,万事或因缘。
肯信神为速,还如静者便。掉头归海岛,障眼扫云烟。
尧舜非无受,羲皇更有前。多岐分炼术,捷径入金仙。
逝者无停息,斯文久绝传。开怀舒浩荡,洗耳藉潺湲。
到处逢膏火,将身赴熬煎。清凉思盥濯,荤血饱腥膻。
大隐金门客,叨陪玉帝筵。全身徒蛰虺,奋击愧高鹯。
瑗过年将迈,予诛志速悛。惭无退日手,犹树彗云鋋。
有客利攸往,何人敢与权。高坚劳钻仰,影响病拘挛。
根本方时发,支离在必蠲。艺游须有息,德猎迅于畋。
观海知无量,窥天失大全。中心秉明哲,和气会相宣。
至德酬知己,高谈谢世贤。庶几犹万一,彷佛见三千。
独步难为继,将开必有先。时贤生衮衮,粤秀起翩翩。
古调诚孤唱,高山未绝弦。流行虽宇宙,鱼兔有蹄筌。
蕴藉胡为者,声名骤隐焉。奎星元朗矅,文运亦回旋。
讨论随毛颖,游居即楮玄。骐骝产渥水,毛羽长青田。
子史如珠贯,经书以类连。玉金声互戛,苕翠色相鲜。
古器看黄吕,和音听铎舷。纷纷惊藻思,稍稍弄云笺。
历块迷途辙,追风累缠牵。同行常似砥,皇路忽如邅。
弃席还当惜,君恩忍遽捐。瓶冰占气候,尺水起漪涟。
枯草知兴废,元龟定涧瀍。七三梅有摽,花柳昼连阡。
去路瞻南斗,归途转北鞭。寿筵舞锦绣,月殿见婵娟。
珠剃先隆翟,峨冠细玩蝉。李桃酬种种,瓜瓞祝绵绵。
家徒四白壁,业有一青毡。永怀梁子节,不愧孟光钿。
牧犊心悲雉,东莱笔胜椽。光生魁堡里,华发秀山巅。
泉石宁耽恋,膏肓可疗痊。依依看院草,冉冉见池莲。
倒蔗渐如境,么荷苦似拳。会前釐室席,已兆讲堂鳣。
尘土浑缁素,风埃没锦鞯。灵源殊濯濯,静溜自涓涓。
习静依山下,行歌到海壖。大醒尘土梦,勇斩葫芦缠。
閒倚孤崖啸,魂酣绝嶂眠。未须游远骑,祇合坐中坚。
花发馨香远,云开锦绮妍。抢榆无大翼,止棘是轻翾。
允矣谁能拔,招之或以旃。尘头障霾雾,足底动星躔。
衾影恒存畏,盘盂亦致虔。至人无彼我,举世入陶甄。
谁捧寻常土,时方四六骈。醯鸡生翰简,负蝂累尘编。
开户誇新学,名家业旧专。诚能通内外,不必佩韦弦。
槁槁修形客,泠泠古寺禅。到头还自得,入手要求诠。
蜀犬多骇日,南辕岂适燕。十千凭奋迅,九万快高骞。
看剑歌还叠,拈杯语更延。途危防骥足,江涨慑蛟涎。
西土无仪凤,南州有杜鹃。笔谈先远寓,书舫蚤言还。
蹈海休从鲁,寻山谩觅佺。临流悲影独,涉水惜裳褰。
渊静忻潜鲤,天空看戾鸢。如君多直谅,合我补遗愆。
壶子机将杜,西铭意独镌。王孙何伥伥,芳草又芊芊。
远到仍胜重,孤征岂惮孱。为言同志子,共赴胜流铨。
(1466—1560)广东增城人,字元明,号甘泉。少师事陈献章。弘治十八年进士,授编修。历南京国子监祭酒,南京吏、礼,兵三部尚书。在翰林院时与王守仁同时讲学,主张“随处体认天理”,“知行并进”,反对“知先行后”,与阳明之说有所不同。后筑西樵讲舍讲学,学者称甘泉先生。卒谥文简。著有《心性图说》、《格物通》、《甘泉集》等。
经,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其应乎感也,则为恻隐,为羞恶,为辞让,为是非;其见于事也,则为父子之亲,为君臣之义,为夫妇之别,为长幼之序,为朋友之信。是恻隐也,羞恶也,辞让也,是非也,是亲也,义也,序也,别也,信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阴阳消息之行焉,则谓之《易》;以言其纪纲政事之施焉,则谓之《书》;以言其歌咏性情之发焉,则谓之《诗》;以言其条理节文之著焉,则谓之《礼》;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则谓之《乐》;以言其诚伪邪正之辩焉,则谓之《春秋》。是阴阳消息之行也以至于诚伪邪正之辩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夫是之谓六经。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经也,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所以尊《书》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所以尊《诗》也;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著焉。所以尊《礼》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所以尊《乐》也;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辩焉,所以尊《春秋》也。
盖昔者圣人之扶人极、忧后世而述六经也,犹之富家者之父祖,虑其产业库藏之积,其子孙者或至于遗忘散失,卒困穷而无以自全也,而记籍其家之所有以贻之,使之世守其产业库藏之积而享用焉,以免于困穷之患。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记籍者,特名状数目而已。而世之学者,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是犹富家之子孙,不务守视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日遗忘散失,至于窭人丐夫,而犹嚣嚣然指其记籍。曰:“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何以异于是?
呜呼!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淫辞,竞诡辩,饰奸心盗行,逐世垄断,而犹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若是者,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宁复知所以为尊经也乎?
越城旧有稽山书院,在卧龙西岗,荒废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于民,则慨然悼末学之支离,将进之以圣贤之道,于是使山阴令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又为尊经之阁于其后,曰: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阁成,请予一言,以谂多士。予既不获辞,则为记之若是。呜呼!世之学者,得吾说而求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为尊经也矣。
莺花寨近来谁战讨,这儿郎悬宝剑佩金貂。燕子楼屯合着铠甲,鸡儿巷簇拥
着枪她。丽春园万马萧萧,鸣珂巷众口嗷嗷,将一座玩江楼等闲白占了。他道是
特钦丹招,穿花掖凤鸟,跨海斩鲸鳌。
【逍瑶乐】六韬三略,也则待制胜量敌,却做了幽期密约。阵马咆哮,比贩
茶船煞是粗豪,将俺这软弱苏卿禁害倒。统领着鸦青神道,将散蜂媒蝶使,烘散
燕子莺儿,拆散凤友鸾交。
【梧叶儿】虽不是糟糠妇,休猜做花月妖。又不曾谙海岛惯风涛,把舵春纤
嫩,扶篙筋力小。恁待去征辽,没话说军期误却。
【金菊香】
他将绛绡裙笼罩着锦征袍,银铠甲缨联着珠络索,铁兜鍪压损了金凤翘。改
尽了风标,全不似海棠娇。
【醋葫芦】枪攒呵玉臂擎,箭来呵罗袜挑。丁香舌叶似剑吹毛,连珠炮被窝
儿里聒破脑。知音的都道,我不信建头功先奏你个女妖娆。
【二】铰青丝缠做弩弦,裁香罗衲做战袄。补旗幡绞断翠裙腰,金疮药细将
脂粉调。都是些风流功效,他则想五花诰飞下紫宸朝。
【三】叫喳喳锦缆移,闹垓垓画桨摇。那里取明眸皓齿姆军稍,更做道孙武
子教得来武艺高。止不过提铃喝号,抵多少碧桃花下坐吹箫。
【四】他恋着篷窗下风致佳,舵楼中景物饶。棹歌声里乐陶陶,辱没杀铺红
苦绿翡翠巢。怕不道相偎相抱,那里也芙蓉帐暖度春宵。
【五】晚风凉篥鸣,晓星沉鼙鼓敲。热乐似银筝象板紫檀槽,则学的君起
早时臣起早。白鸥冷笑,倒惹的黑漫漫杀气蜃楼高。
【随煞】奶奶得了些卖阵钱,哥哥占了些劳军钞。他向这海神庙多买好香烧,
但只愿一年一度征海岛。休忘了将军的旗纛,他是个玉门关旧日的莽班超。 客窗值雪
倚龙泉数声长叹息,游子去何期。添一岁长一分白发,治一经饱一世黄齑。
风凛凛岁晚江空,雪漫漫天阔云低。对梅花叹人犹未归,观不足严凝景致。玉壶
春滟滟,银海夜凄凄。
【逍遥乐】
客窗深闭,止不过香炷龙涎,茶烹风髓,纸帐低垂。早难道翠倚红偎,冷暖
年来只自知,捱不彻凄凉滋味。鸳鸯无梦,鸿雁无音,灵鹊无依。
【金菊香】看别人吹箫跨凤上瑶池,乘兴扁舟访剡溪。真仍是平地白云三万
里,堪画堪题。水晶宫翻做素玻璃。
【尾声】调琴演楚骚,研朱点《周易》。风流似党进,终日醉如泥。磨龙香
拂花笺呵冻笔,挥写就乾坤清气,着人道老袁安犹自说兵机。
【般涉调】哨遍 新建构栏教坊求赞
圣遍飞龙当日,火精焰焰光天德。三尺剑一戎衣,笑谈间平吞了万里华夷。
二气里,八荒跻寿。四海涵春,酉酉出雍熙治。都会金陵佳丽,鲁麟呈瑞,周凤
来仪。天香荡酒旗风,甘露调和落花泥。拽塌了旌旗,打灭了烽尘,销溶了剑
戟。
【耍孩儿】赤紧的教坊司独占了阳和地,越显得莺花艳美。真乃是紫微宫殿
乐星集,另巍巍创立个根基。方位里都按着郭景纯经天伟地阴阳诀,规矩上不离
了鲁公输迈古超今造化机。昏昼里无休息,响玎玎斧斤电掣,闹垓垓锯铲星飞。
【七煞】瓦砾披荡的平,风火墙垒砌得疾,百年便作千年计。选良材砍尽
了南山铁干霜皮木,搬巨磉捞遍了东海金星雪浪石。非容易,半空中觚棱□耸,
平地上轮奂光辉。
【六煞】上设着透风月玲珑八向窗,下布着滴星辰嵯峨百尺梯,俯雕栏目穷
天堑三千里。障风檐细粼粼檐牙高展文鸳翅,飞云栋碜可可檐角高舒恶兽尾。多
形势,碧窗畔荡悠悠暮云朝雨,朱帘外滴溜溜北斗南箕。
【五煞】门对着李太白写新诗凤凰千尺台,地绕着张丽华洗残妆胭脂一派水,
敞南轩看不尽白云掩映钟山翠。三尺台包藏着屯莺聚燕闲入窟,十字街控带着踞
虎盘龙旧帝基。柳影浓花阴密,过道儿紧栏着朱雀,招牌儿斜拂着乌衣。
【四煞】这壁厢酒肆里笙歌聒耳来,那壁厢厢渲房中麝兰扑鼻吹,隔离五云
宫阙无多地。鼓儿敲普冬冬响随仙仗迎□□,板儿撒礻乞剌剌声逐天风入凤墀。
八音备:土匏革木,丝竹金石。
【三煞】豁达似彩霞观金碧妆,气概似紫云楼珠翠围,光明似辟寒台水晶宫
里秋无迹,虚敞似广寒上界清虚府,廊□□兜率西方极乐国。多华丽,潇洒似蓬
莱岛琳宫绀宇,风流似昆仑山紫府瑶池。
【二煞】捷剧每善滑稽能戏设,引戏每叶宫商解礼仪,妆孤的貌堂堂雄纠纠
口吐虹霓气。付末色说前朝论后代演长篇歌短句江河口颊随机变,付净色腆嚣庞
张怪脸发乔科店冷诨立木形骸与世违。要扌朵每未东风先报花消息,妆旦色舞
态袅三眠杨柳,末泥色歌啖撒一串珍珠。
【一煞】王孙每意悬悬怀揣着赏金,郎君每眼巴巴安排着庆赏囗,跳龙门题
雁塔悬羊头踏狗尾一个个皆随喜。扎礻覃的亚着肩叠着脊倾着囊倒着产大拚白雪
银双镒,妆孤的争着头鼓着脑舒着眉睁着眼细看春风玉一围。权当个门山日,名
扬北冀,声播南陲。
【尾】托赖着九重雨露恩,两轮日月辉。这构栏领莺花独镇着乾坤内,便一
万座梁园也到不得。
人生最苦别离,柳系柔肠,山敛愁眉。金缕歌残,青衫泪湿,锦字来迟。留客醉鱼肥酒美,送春行莺老花飞。此恨谁知?今夜相思,何日归期?
幽居
红尘不到山家,羸得清闲,当了繁华。画列青山,茵铺细草,鼓奏鸣蛙。杨柳村中卖瓜。蒺藜沙上看花。生计无多,陶令琴书,杜曲桑麻。
西陵送别
画船儿载不起离愁,人到西陵,恨满东州。懒上归鞍,情开泪眼,怕倚层楼。春去春来,管送别依依岸柳。潮生潮落、会忘机泛泛沙鸥。烟水悠悠,有句相酬,无计相留。
夜景
小红楼独倚新妆,曲角阑干,嫩绿池塘。雨洗花梢,风梳柳影,月荡荷香。绣枕上双飞凤凰,翠蓬边一只鸳鸯。对景情伤。今夜新凉,何处才郎?
金华山看瀑泉
碧桃花流出人间,一派冰泉,飞下仙山。银阙峨峨,琼田漠漠,玉珮珊珊。朝素月鸾鹤夜阑,拱香云龙虎秋坛。人倚高寒,字字珠玑,点点琅玕。
别情
倒金杯檀口娇羞,春柳垂腰,秋水凝眸。满意温存,通身旖旎,彻胆风流。秋千院同携玉手,琵琶亭催解兰舟。无计相留,别后新词,总是离愁。
晚春送别
借旗亭仙子逢迎,舞态飞琼,歌韵流莺。红线幽欢,乌丝小字,金缕新声。留过客江山有灵,废残春风雨无情。花落闲庭,柳暗空城。今夜离别,后日清明。
和疏斋学土韵
爱疏仙不放春闲,坐玉树词林,镜海仙山。花老南枝,雪深西圃,人倚东阑。煨芋人吟翁正懒,出蓝关迁客当寒。绿酒酡颜。银字春葱,彩凤娇鬟。
游太乙宫
华山高与云齐,远却尘埃,睡煞希夷。踏藕童闲,携琴客至,跨鹤人归。鸣玉珮松溪活水,点冰绡竹院枯梅。短策徘徊,醉墨淋漓,老技崔嵬。
游金山寺
倚苍云绀宇峥嵘,有听法神龙,渡水胡僧。人立冰壶,诗留玉带,塔语金铃。摇碎月中流树影,撼崩崖半夜江声。误汲南冷,笑杀吴侬,不记茶经。
秦邮即事
访秦邮暂驻兰桡,浩荡鸥波,缥缈虹桥。白藕翻根,黄芦颤叶,翠柳搴条。照玉女神仙井小,立金人菩萨台高。散策逍遥,酒市歌云,僧院诗巢。
皆春楼
柳依依重屋峨峨,媚景芳研,四序无过。雾暖朱帘,风喧翠槛,露湛金荷。天地德无分物我,花草香总是阳和。乐事如何?明月交辉,白雪扬歌。
湖上饮别
傍垂杨画舫徜徉,一片秋怀,万顷晴光。细草闲鸥、长云小雁,乱苇寒螀。难兄难弟俱白发相逢异乡,无风无雨未黄花不似重阳。歌罢沧浪,更引壶觞,送别河梁。
春情
寄春情小字亲描,体态宫蛾,艳冶花妖。映雪香肌,堆云巧鬓,抱月纤腰。嬴女伴一场斗草,指仙翁三度偷桃。羞弄生绡,懒上秋千,笑整金翘。
次酸斋韵
倚阑干不尽兴亡,数九点开州,八景湘江。吊古词香,招仙笛响,引兴杯长。远树烟云渺茫,空山雪月苍凉。白鹤双双,剑客昂昂,锦语琅琅。
闺思
怕别离真个别离,不得音书,已误芳菲。曲怨金徽,香销翠被,梦断罗帏。湿马蹄残红似泥,接莺巢浓绿成堆。消瘦冰肌,体画蛾眉,直待他归。
别后
一年余凤只鸾孤,枕上嗟吁,镜里清癯。花已飘然,春将暮矣,各未归欤。啼翠霭林间鹧鸪,坠青丝檐外蜘蛛。既在江湖,有便鳞鸿,不寄音书。
酒边分得卿字韵
客留情春更多情,月下金觥,膝上瑶筝。口口声声,风风韵韵,袅袅亭亭。锦胡洞莺招燕请,玉交枝柳送花迎。不负平生,风月坡仙,诗酒耆卿。
江上次刘时中韵
倚篷窗一笑诗成,远寺昏钟,古渡秋灯。隐隐鸣鼍。嗷嗷旅雁,闪闪飞萤,海树黑风号浪惊,越山青月暗云生。书客飘零,欲泛仙槎,试问君平。
逢天坛子
正吟诗马上逢君,昨暮秦关,今日吴门。绣帽攲风,金鞭拂雪,宝挑靪云。江上花恼人,堤边柳眼窥春。便洗征尘,借问前村,试买芳博。
皆山楼即事
爱楼居四面皆山,图画横陈,步障回还。远村重重,幽花淡淡,小竹珊珊。黄卷掩灯青夜阑,紫箫吹月白凤寒。鹤唳云间,人倚阑干,欲泛仙槎,直扣天关。
次白真人韵
葛花袍纸扇芭蕉,两袖仙风,万古诗豪。富贵劳劳,功名小小,车马朝朝。算只有青山不老,是谁教白发相饶?体负良宵,百斛金波,一曲琼箫。
歌姬施氏
照冰壶秋水芙蕖,姓出西家,名满东吴。鸾镜妆残,霓裳曲破,翠管诗余。娇滴滴眉云眼雨,香馥馥腕玉胸酥。同醉仙都,偷寄银笺,暗解罗襦。
重午席间
浴兰芳荆楚风流,艾掩门眉,符映钗头。雪卷鸥波,雷轰鼍鼓,电闪龙舟。骄马骤雕弓翠柳,小蛾讴宝髻红榴。醉倚江楼,笑煞湘累,不葬糟丘。
幽居次韵
石帆山下吾庐,秋水纶竿,落日巾车。长啸归欤,梅惊花谢,柳笑眉舒。撺断著小丫鬟舞元宵迓鼓,摸索著大肚皮装村酒葫芦。冷落琴书,结好樵渔,是有红尘,不到幽居。
想翠竹、碧梧风采,旧游何处。
三径西风秋共老,满庭疏雨春都过。
看苍苔、白石易黄昏,愁无数。
峄山畔,淇泉路。空回首,佳期误。
叹舞鸾鸣凤,归来迟暮。
冷淡还如西草,凄迷番作江东树。
且留他、素管候冰丝,重相和。
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湛若水
湛若水 王守仁
王守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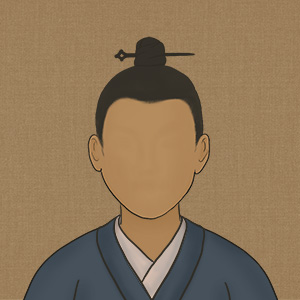 汤舜民
汤舜民 张可久
张可久 马致远
马致远 吕本中
吕本中 张宁
张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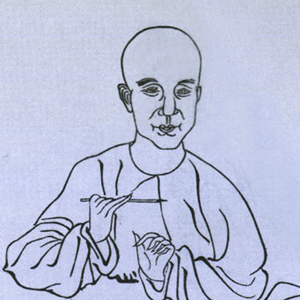 项鸿祚
项鸿祚 辛弃疾
辛弃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