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创作背景
赏析
南朝梁南兰陵(今江苏常州)人,字景光,萧子恪弟。少涉书史,有文才。起家员外散骑侍郎,迁南中郎记室。出为临安、新繁令。官终骠骑长史。曾听梁武帝讲《三慧经》,退作《讲赋》上奏,为武帝称赏。性恬静、寡嗜欲。有集已佚。
猜您喜欢
十年不到湖山,齐楚秦燕,皓首苍颜。今日重来,莺嫌花老,燕怪春悭。听
越女鸾箫象板,恼司空雾鬓云环。道院弹关,酒会诗坛,万古西湖,天上人间。 钱子云赴都
赋河梁渺渺予怀,今日阳关,明日秦淮。鹏翼风云,龙门波浪,马足尘埃。
宽洗汕胸中四海,便蜚腾天上三台。休等书斋,梅子花开,人在江南,先寄诗来。 江淹寺
紫霜毫是是非非,万古虚名,一梦初回。失又何愁?得之何喜?闷也何为?
落日外萧山翠微,小桥边古寺残碑。文藻珠玑,醉墨淋淳,何似班超,投却毛锥。 登太和楼
白云中涌出蓬莱,俯视西湖,图画天开。暮雨珠帘,朝云画栋,夜月瑶台。
书籍会三千剑客,管弦声十二金钗。对酒兴杯,拊髀怜才,寄语玲珑,王粲曾来。 竹夫人
湘妃应是前身,不记何年,封虢封秦。万古虚心,百年贞节,一世故人。剖
苍壁寒凝泪痕,挽潜蛟巧结香纹。侍枕知恩,入梦无春,两腋清风,满枕行云。 姑苏台
荒台谁唤姑苏?兵渡西兴,祸起东吴。切齿仇冤,捧心钓饵,尝胆权谋。三
千尺侵云粪土,十万家泣血膏腴。日月居诸,台殿丘墟。何似灵岩,山色如初。 名姬玉莲
荆山一片玲珑,分付冯夷,捧出波中。白羽香寒,琼衣露重,粉面冰融。知
造化私加密宠,为风流洗尽娇红。月对芙蓉,人在帘栊。太华朝云,太液秋风。 春情
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身似浮云,心如飞絮,气若游丝。空
一缕余香在此,盼千金游子何之。证候来时,正是何时?灯半昏时,月半明时。 西湖寻春
清明春色三分,湖上行舟,陌上游人。一片花阴,两行柳影,十里莎ブ。不
要多ゾ排一品,休嫌少酒止三巡。处处开樽,步步寻春。花下归来,带月敲门。 送沙宰
宦游人过钱塘,江水汤汤,山色苍苍。马首西风,鸡声残月,雁影斜阳。男
子志周流四方,循吏心恪守三章。岐麦林桑,渡虎驱蝗。人颂《甘棠》,春满琴
堂。 月
问青天呼酒重倾,几度盈亏,几度阴晴。夜冷鱼沉,山空鹤唳,露滴乌惊。
看杨柳楼心弄影,听梨花树底吹笙。雪与争明,风与双清。玉兔韬光,万古长生。 赠粉英
温柔乡里娉婷,清比梅花,更有余清。玉蕊含香,琼蕤沁月,瑶萼裁冰。冠
杨柳东风媚景,赋芙蓉夜月幽情。花下苏卿,月下崔莺,世上飞琼,天上双成。 西湖夏宴
卷荷筒翠袖生香,忙处投闲,静处寻凉。一片歌声,四围山色,十里湖光。
只此是人间醉乡,更休题天上天堂。老子疏狂,信手新词,赠与秋娘。 红梅
蕊珠宫内琼姬,醉倚东风,谁与更衣?血泪痕深,茜裙香冷,粉面春回。桃
杏色十分可喜,冰霜心一片难移。何处长笛?吹散胭脂,分付春归。
越女鸾箫象板,恼司空雾鬓云环。道院弹关,酒会诗坛,万古西湖,天上人间。 钱子云赴都
赋河梁渺渺予怀,今日阳关,明日秦淮。鹏翼风云,龙门波浪,马足尘埃。
宽洗汕胸中四海,便蜚腾天上三台。休等书斋,梅子花开,人在江南,先寄诗来。 江淹寺
紫霜毫是是非非,万古虚名,一梦初回。失又何愁?得之何喜?闷也何为?
落日外萧山翠微,小桥边古寺残碑。文藻珠玑,醉墨淋淳,何似班超,投却毛锥。 登太和楼
白云中涌出蓬莱,俯视西湖,图画天开。暮雨珠帘,朝云画栋,夜月瑶台。
书籍会三千剑客,管弦声十二金钗。对酒兴杯,拊髀怜才,寄语玲珑,王粲曾来。 竹夫人
湘妃应是前身,不记何年,封虢封秦。万古虚心,百年贞节,一世故人。剖
苍壁寒凝泪痕,挽潜蛟巧结香纹。侍枕知恩,入梦无春,两腋清风,满枕行云。 姑苏台
荒台谁唤姑苏?兵渡西兴,祸起东吴。切齿仇冤,捧心钓饵,尝胆权谋。三
千尺侵云粪土,十万家泣血膏腴。日月居诸,台殿丘墟。何似灵岩,山色如初。 名姬玉莲
荆山一片玲珑,分付冯夷,捧出波中。白羽香寒,琼衣露重,粉面冰融。知
造化私加密宠,为风流洗尽娇红。月对芙蓉,人在帘栊。太华朝云,太液秋风。 春情
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身似浮云,心如飞絮,气若游丝。空
一缕余香在此,盼千金游子何之。证候来时,正是何时?灯半昏时,月半明时。 西湖寻春
清明春色三分,湖上行舟,陌上游人。一片花阴,两行柳影,十里莎ブ。不
要多ゾ排一品,休嫌少酒止三巡。处处开樽,步步寻春。花下归来,带月敲门。 送沙宰
宦游人过钱塘,江水汤汤,山色苍苍。马首西风,鸡声残月,雁影斜阳。男
子志周流四方,循吏心恪守三章。岐麦林桑,渡虎驱蝗。人颂《甘棠》,春满琴
堂。 月
问青天呼酒重倾,几度盈亏,几度阴晴。夜冷鱼沉,山空鹤唳,露滴乌惊。
看杨柳楼心弄影,听梨花树底吹笙。雪与争明,风与双清。玉兔韬光,万古长生。 赠粉英
温柔乡里娉婷,清比梅花,更有余清。玉蕊含香,琼蕤沁月,瑶萼裁冰。冠
杨柳东风媚景,赋芙蓉夜月幽情。花下苏卿,月下崔莺,世上飞琼,天上双成。 西湖夏宴
卷荷筒翠袖生香,忙处投闲,静处寻凉。一片歌声,四围山色,十里湖光。
只此是人间醉乡,更休题天上天堂。老子疏狂,信手新词,赠与秋娘。 红梅
蕊珠宫内琼姬,醉倚东风,谁与更衣?血泪痕深,茜裙香冷,粉面春回。桃
杏色十分可喜,冰霜心一片难移。何处长笛?吹散胭脂,分付春归。
过眼溪山,怪都似、旧时相识。还记得、梦中行遍,江南江北。佳处径须携杖去,能消几緉平生屐。笑尘劳、三十九年非、长为客。
吴楚地,东南坼。英雄事,曹刘敌。被西风吹尽,了无尘迹。楼观才成人已去,旌旗未卷头先白。叹人间、哀乐转相寻,今犹昔。
吴楚地,东南坼。英雄事,曹刘敌。被西风吹尽,了无尘迹。楼观才成人已去,旌旗未卷头先白。叹人间、哀乐转相寻,今犹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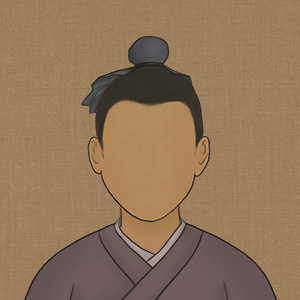 萧子晖
萧子晖 冯梦龙
冯梦龙 王恽
王恽 白朴
白朴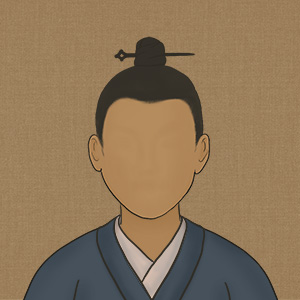 徐再思
徐再思 元好问
元好问 李好古
李好古 吴锡麒
吴锡麒 温庭筠
温庭筠 辛弃疾
辛弃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