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赋
草弱朱靡,水夕沉鳞。又碧月兮河粱,秋风兮在林。
指金闺于素璧,向翠幔于琴心。于此言别,怀愁不禁。
云泫泫兮似浮,泉杳杳而始下。抚檐幄之霏凉,拂银筝其孰写。
重以伭花之早寒,玉台之绛粉。既解佩而邅延,更留香之氤氲。
揽红药之夜明,怅青兰而晨恨。会当远友,瞻望孤云。
于是明河欲坠,玉勒半盼。化桃霞兮王孙马,冲柳雪兮游子衣。
离远皋之木叶。牵睛[晴]雾之游丝。度疏林而去我,隔江水之微波。
本平夷而起巘,更通达而成河。妍迹已往,遗恩在涂。
掩电母而不御,杂水业而常孤。思美人兮江溆,触鸾发兮愁余。
并瑶瑟之潺湲。共风吹而无娱。念众族之皎皎,独与予兮纷驰。
谁径逝而不顾,怀缥缈而奚知。诚自悲忧,不可言喻。
更若玄圃词人,洛滨才子。收车轮于博望,荡云物于龙池。
嘉核甫陈,骊歌遽奏。折银蕊于陇上,骄箫馆于池头。
之官京洛,迁斥罗浮。观大旗之莫射。登金谷而不游。
叹木瓜之溃粉,聆悽响于清辀。或朔零陵之事,或念南皮之俦。
咸辞成而琅琅,视工思而最愁。又若河朔少年,南阳乳虎。
感乌马兮庭阶,击苍鹰兮殿上。风戋戋兮渐哀。筑摵摵而欲变。
仁客敛魂,白衣数起。左骖殪兮更不还,黄尘合兮心所为。
忽日昼之晻暧,睹寒景之侵衣。愁莫愁兮众不知,悲何为兮悲壮士。
乃有十年陷敌,一剑怀仇。将置身于广柳,或髡钳而伏匿。
共衰草兮班荆,咽石濑兮设食。逝泛滥于重渊,旷霅煜于窋室。
酒未及潺,餐末及下。歌河上而沾裳,仰驷沫而太息。
若吴门之篪,意本临岐。大梁之客,魂方逝北。当起舞而徘徊,更痛深其危戚。
至若掩纨扇于炎州,却真珠厂玉漏、恩甚兮忽绝,守礼兮多尤。
观蒻羽之拂璧,慨龙帷之郁留,念胶固而独明,惟销铄之莫任。
垂楚组而扰倚,絙凤绶而遣神。盼雉尾于俄顷,迥金螭之别深。
日暮广陵,凭栏水调。似殿台之清虚,识宜春之朗曼。
乃登舟而呜咽,愁别去其漫漫。又若红粉羽林,辟邪独赐。
同武帐之新宠,后灞岸之放归。紫萧兮事远,金缕兮泪滋。
更若长积雪兮闭青冢,嫁绝域兮永乌孙。俨云蝉于万里,即烟霓之夕昏。
雁山晓兮断辽水。红蕉涩兮辞婵嫒。至若灵娥九日兮将梳,苕蓉七夕兮微渡。
月映晰而创虹缕,露流澌兮开房河。披天衣之霄叙,忽云旗之怅图。
亦有托纤阿于淄右,期玉镜于邯郸。甫珊瑚之照耀,亲犀珞之缠绵。
悼亭上之春风,叹上巳于玉面。本独孤之意邈,绕窦女之情娟。
至有虾蟆陵下之歌,燕子楼前之雨。白杨萧萧兮莺冢灰,莓苔瑟瑟兮四陵上。
怆虬膏之水诀,淡华烛而终古。顾骖驔之奠攀,止玉合之荐处。
岂若西园无忌,南国莫愁,始承欢面不替,卒旷然而不违。
君歌折柳于郑风,妾咏蘼芜于天外。异樱桃之夜语,非洛水之朝来。
自罘罳之雀暗,怜兰麝之鸭衰。据青皋之如昨,看盘马之可哀。
招摇蹀躞,花落徘徊。结绶兮在平乐,言别号登高台。
君有旨酒,妾有哀音,为弹一再,徒伤人心。悲夫同在百年之内,共为幽怨之人。
事有参商,势有难易。虽知己而必别,纵暂别其必深。
冀白首而同归,愿心志之固贞。庶乎延平之剑,有时而合。
平原之簪,永永其不失矣。
柳如是(1618年~1664年),明末清初女诗人,本名杨爱,字如是,又称河东君,因读宋朝辛弃疾《贺新郎》中:“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故自号如是。浙江嘉兴人。柳如是是明清易代之际的著名歌妓才女,幼即聪慧好学,但由于家贫,从小就被掠卖到吴江为婢,妙龄时坠入章台,改名为柳隐,在乱世风尘中往来于江浙金陵之间。留下的作品主要有《湖上草》、《戊寅草》与《尺牍》。
隋舰临淮甸,唐旗出井陉。断鳌支四柱,卓马济三灵。
祖业隆盘古,孙谋复大庭。从来师俊杰,可以焕丹青。
旧族开东岳,雄图奋北溟。邪同獬廌触,乐伴凤凰听。
酣战仍挥日,降妖亦斗霆。将军功不伐,叔舅德惟馨。
鸡塞谁生事,狼烟不暂停。拟填沧海鸟,敢竞太阳萤。
内草才传诏,前茅已勒铭。那劳出师表,尽入大荒经。
德水萦长带,阴山绕画屏。秖忧非綮肯,未觉有膻腥。
保佐资冲漠,扶持在杳冥。乃心防暗室,华发称明廷。
按甲神初静,挥戈思欲醒。羲之当妙选,孝若近归宁。
月色来侵幌,诗成有转棂。罗含黄菊宅,柳恽白蘋汀。
神物龟酬孔,仙才鹤姓丁。西山童子药,南极老人星。
自顷徒窥管,于今愧挈瓶。何由叨末席,还得叩玄扃。
庄叟虚悲雁,终童漫识艇。幕中虽策画,剑外且伶俜。
俣俣行忘止,鳏鳏卧不瞑。身应瘠于鲁,泪欲溢为荣。
禹贡思金鼎,尧图忆土铏。公乎来入相,王欲驾云亭。
出镇淮门,循小秦淮折而北,陂岸起伏多态,竹木蓊郁,清流映带。人家多因水为园亭树石,溪塘幽窃而明瑟,颇尽四时之美。拿小艇,循河西北行,林木尽处,有桥宛然,如垂虹下饮于涧;又如丽人靓妆袨服,流照明镜中,所谓红桥也。
游人登平山堂,率至法海寺,舍舟而陆径,必出红桥下。桥四面触皆人家荷塘。六七月间,菡萏作花,香闻数里,青帘白舫,络绎如织,良谓胜游矣。予数往来北郭,必过红桥,顾而乐之。
登桥四望,忽复徘徊感叹。当哀乐之交乘于中,往往不能自喻其故。王谢冶城之语,景晏牛山之悲,今之视昔,亦有怨耶!壬寅季夏之望,与箨庵、茶村、伯玑诸子,倚歌而和之。箨庵继成一章,予以属和。
嗟乎!丝竹陶写,何必中年;山水清音,自成佳话,予与诸子聚散不恒,良会未易遘,而红桥之名,或反因诸子而得传于后世,增怀古凭吊者之徘徊感叹如予今日,未可知者。
娇面。 蹴リ
软履香泥润,轻衫香雾湿,几追陪五陵豪贵。脚到处春风步步随,占人间一
团和气。 梅女吹箫图
髻青螺小,钗横玉燕低,背东风为准凝睇。闲拈凤箫不待吹,恐梅花等闲
飘坠。
些些并蒂红,指指连枝翠。悭悭金谷路,窄窄五陵溪。一片花飞,泄漏春消息。舞盘中歌扇底,刮得尽风月无多,趱得过繁华有几?
【梁州第七】一两个莺俦燕侣,五七双蝶使蜂媒。窖来宽也称游人戏。眼孔大刘晨未识,脚步长杜甫先迷。画帧上香销粉滴,镜奁中绿暗红稀。唾津儿浸满盆池,手心儿擎得起屏石。苔钱儿买不断闲愁,花瓣儿随手着流水,柳丝儿送不够别离。锦堆,翠积。海棠偷足相思睡,名偏小景偏媚。赚得东君不忍归,一撮儿芳菲。
【余音】楚阳台云雨无三尺,桃源洞光阴减九十。玉拶香挨这窝儿地,堪信道一寸阴可惜。千金价总宜,锦步幛何须五十里?
地心劳形役。量这些来小去官职,枉消磨了浩然之气。
【醉春风】想聚散若浮云,叹光阴如过隙。不如闻早赋归欤,畅是一个美,
美。弃职归农,杜门修道,早则死心搭地。
【红绣鞋】泛远水舟遥遥以轻,送征帆风飘飘而吹衣,望烟水平芜把我去
程迷。问征夫询远近,瞻衡日熹微,盼柴桑归兴急。
【满庭芳】再休想折腰为米,落得个心闲似水,酒醉如泥。乐并不管家
和计,都分付与稚子山妻。栽五柳闲居隐迹,抚孤松小院徘徊。问因宜把功名弃?
岂不见张良范蠡,这两个多大得便宜。
【上小楼】我则待逐朝每日,无拘无系。我则待从事西畴,寄傲南窗,把酒
东篱。三径就荒,松菊犹存,规模不废,策扶老尚堪流憩。
【幺】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自怡。有酒盈樽,门设常关,景幽人寂。或
命巾车,或棹孤舟,从容游戏,比着个彭泽县较淡中有味。
【耍孩儿】溪泉流出涓涓细,木向阳欣欣弄碧。登东皋舒啸对斜晖,有两般
儿景物希奇。觑无心出岫云如画,见有意投林鸟倦飞。草堂小堪容膝,说亲戚之
情话,乐琴书以忘机。
【幺】或寻丘壑观清致,或自临清流品题。我为甚绝交游待与世相违,须是
我傲羲皇本性难移。想人间富贵非吾愿,望帝里迢遥不可期。已往事都休记,度
晚景乐夫天命,其余更复奚疑。
【尾声】辞功名则待远是非,守田园是我有见识。闲悠悠无半点为官意,一
任驷马高车聘不起。
 柳如是
柳如是 李商隐
李商隐 王士祯
王士祯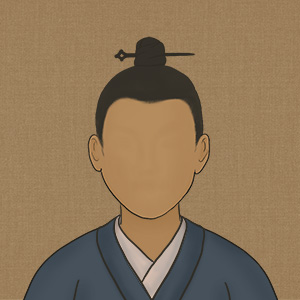 汤舜民
汤舜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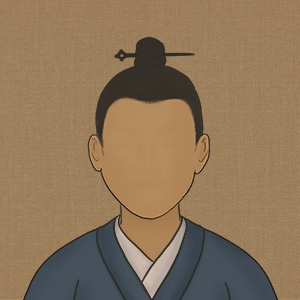 周文质
周文质 薛昂夫
薛昂夫 李致远
李致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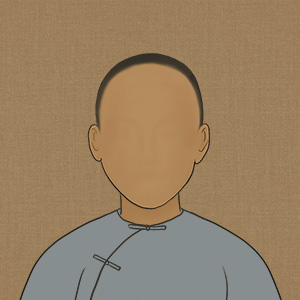 王国维
王国维 纳兰性德
纳兰性德 刘禹锡
刘禹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