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赏析
创作背景
简析
曹邺(约816~875),字业之, 一作邺之,桂州(今广西桂林阳朔)人。晚唐诗人。 与刘驾、聂夷中、于濆、邵谒、苏拯齐名,而以曹邺才颖最佳。曹邺曾担任吏部郎中(唐)、洋州刺史(唐)、祠部郎中(唐)等职务。
猜您喜欢
远归
年深马骨高,尘惨貂裘敝。夜长鸳梦短,天阔雁书迟。急觅归期,不索寻名利。归心紧归去疾,恨不得袅断鞭梢,岂避千山万水!
【梁州】龟卦何须再卜,料灯花已报先知。并程途不甫能来到家内,见庭闲小院,门掩昏闺,碧纱窗悄,斑竹帘垂。将个栊门儿款款轻推,把一个可喜娘脸儿班回。急惊列半晌荒唐,慢朦腾十分认得,呆答孩似醉如痴!又嗔,又喜。共携素手归兰舍,半含笑半擎泪。些儿春情云雨罢,各诉别离。
【尾】我道因思翠袖宽了衣袂,你道是为盼雕鞍减了玉肌。不索教梅香鉴憔悴,向碧纱幮帐底,翠帏屏影里,厮揾着香腮去镜儿比。
看别人鞍马上胡颜,叹自己如尘世污眼。英雄谁识男儿汉,岂肯向人行诉难?
阳气盛冰消北岸,暮云遮日落西山,四时天气尚轮还。秦甘罗疾发禄,姜吕
望晚登坛,迟和疾时运里趱。
阳气盛冰消北岸,暮云遮日落西山,四时天气尚轮还。秦甘罗疾发禄,姜吕
望晚登坛,迟和疾时运里趱。
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送春春去几时回?临晚镜,伤流景,往事后期空记省。
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
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
三万六千顷,玉壶天地寒。
庾岭封的皪,淇园折琅玕。
漠漠梨花烂漫,纷纷柳絮飞残。
直疑潢潦惊翻,斜风溯狂澜。
对此频胜赏,一醉饱清欢。
呼?童翦韭,和冰先荐春盘。
怕东风吹散,留尊待月,倚阑莫惜今夜看。
庾岭封的皪,淇园折琅玕。
漠漠梨花烂漫,纷纷柳絮飞残。
直疑潢潦惊翻,斜风溯狂澜。
对此频胜赏,一醉饱清欢。
呼?童翦韭,和冰先荐春盘。
怕东风吹散,留尊待月,倚阑莫惜今夜看。
一派明云荐爽,秋不住,碧空中响。
如此江山徒莽苍。
伯符耶?
寄奴耶?
嗟已往。
十载羞厮养,孤负煞,长头大颡。
思与骑奴游上党。
趁秋晴,(足庶)莲花,西岳掌。
耿耿秋情欲动,早喷入霜桥笛孔。
快倚西风作三弄。
短狐悲,瘦猿愁,啼破冢。
碧落银盘冻,照不了,秦关楚陇。
无数蛰吟古砖缝。
料今宵,靠屏风,无好梦。
黄叶青苔归路,屧粉衣香何处。消息竟沉沉,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因风吹去。(版本一)
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竟沉沉,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因风吹去。(版本二)
 曹邺
曹邺 白居易
白居易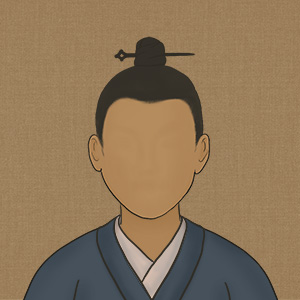 奥敦周卿
奥敦周卿 贯云石
贯云石 张先
张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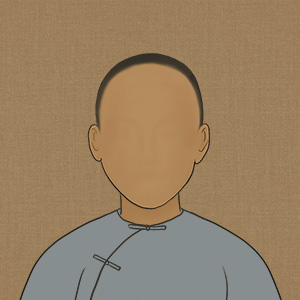 王国维
王国维 张泌
张泌 陈允平
陈允平 陈维崧
陈维崧 纳兰性德
纳兰性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