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赏析
简析
曾公亮(998年-1078年)北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军火家、思想家。字明仲,号乐正,汉族,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市)人。仁宗天圣二年进士,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历官知县、知州,知府、知制诰、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参知政事,枢密使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封兖国公,鲁国公,卒赠太师、中书令,配享英宗庙廷,赐谥宣靖。曾公亮与丁度承旨编撰《武经总要》,为中国古代第一部官方编纂的军事科学百科全书。
猜您喜欢
世情推物理,人生贵适意。想人间造物搬兴废,吉藏凶,凶藏吉。
【夜行船】富贵那能长富贵,日盈昃月满亏蚀。地下东南,天高西北,天地尚无完体。
【庆宣和】算到天明走到黑,赤紧的是衣食。凫短鹤长不能齐,且休题,谁是非。
【锦上花】展放愁眉,休争闲气。今日容颜,老如昨日。古往今来,恁须尽知,贤的愚的,贫的和富的。
【幺】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受用了一朝,一朝便宜。百岁光阴,七十者稀。急急流年,滔滔逝水。
【清江引】落花满院春又归,晚景成何济!车尘马足中,蚁穴蜂衙内,寻取个稳便处闲坐地。
【碧玉箫】乌兔相催,日月走东西。人生别离,白发故人稀。不停闲岁月疾,光阴似驹过隙。君莫痴,休争名利。幸有几杯,且不如花前醉。
【歇拍煞】恁则待闲熬煎、闲烦恼、闲萦系、闲追欢、闲落魄、闲游戏。金鸡触祸机,得时间早弃迷途。繁华重念箫韶歇,急流勇退寻归计。采蕨薇,洗是非;夷齐等,巢由辈。这两个谁人似得?松菊晋陶潜,江湖越范蠡。
【夜行船】富贵那能长富贵,日盈昃月满亏蚀。地下东南,天高西北,天地尚无完体。
【庆宣和】算到天明走到黑,赤紧的是衣食。凫短鹤长不能齐,且休题,谁是非。
【锦上花】展放愁眉,休争闲气。今日容颜,老如昨日。古往今来,恁须尽知,贤的愚的,贫的和富的。
【幺】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受用了一朝,一朝便宜。百岁光阴,七十者稀。急急流年,滔滔逝水。
【清江引】落花满院春又归,晚景成何济!车尘马足中,蚁穴蜂衙内,寻取个稳便处闲坐地。
【碧玉箫】乌兔相催,日月走东西。人生别离,白发故人稀。不停闲岁月疾,光阴似驹过隙。君莫痴,休争名利。幸有几杯,且不如花前醉。
【歇拍煞】恁则待闲熬煎、闲烦恼、闲萦系、闲追欢、闲落魄、闲游戏。金鸡触祸机,得时间早弃迷途。繁华重念箫韶歇,急流勇退寻归计。采蕨薇,洗是非;夷齐等,巢由辈。这两个谁人似得?松菊晋陶潜,江湖越范蠡。
 曾公亮
曾公亮 白居易
白居易 刘墉
刘墉 关汉卿
关汉卿 毛滂
毛滂 毛奇龄
毛奇龄 纳兰性德
纳兰性德 辛弃疾
辛弃疾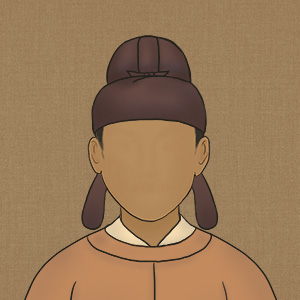 黄公绍
黄公绍